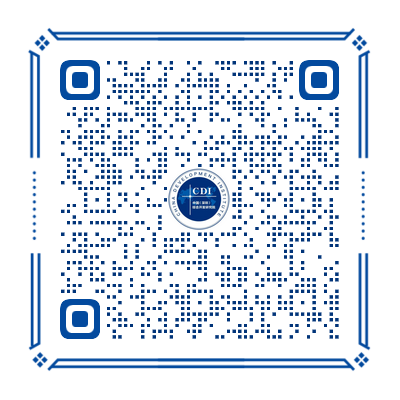近日,德國聯(lián)盟黨總理候選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成功就任德國總理。新政府的到來預(yù)示著德國內(nèi)外政策正步入轉(zhuǎn)型期。在此次聯(lián)盟黨與社民黨達(dá)成的聯(lián)合執(zhí)政協(xié)議《對德國的責(zé)任》中,新政府對外政策的“歐洲化”色彩濃厚。這一轉(zhuǎn)向既是歷史慣性的延續(xù),更是德國在多重壓力下的務(wù)實之舉。作為歐盟的核心成員,德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不僅關(guān)乎其在歐洲舞臺的角色定位,也將對歐盟對華戰(zhàn)略以及中歐關(guān)系產(chǎn)生重要影響。
一、德國對外政策“歐洲化”:凝聚共識的現(xiàn)實選擇?
當(dāng)前,默茨政府面臨經(jīng)濟(jì)持續(xù)低迷、能源價格高企、制造業(yè)承壓、財政負(fù)擔(dān)沉重等多重挑戰(zhàn)。默茨經(jīng)歷的艱難組閣和選舉風(fēng)波也揭示了德國政治生態(tài)的深層裂痕,如執(zhí)政聯(lián)盟的財政政策分歧、極右翼政黨的崛起、民眾對經(jīng)濟(jì)復(fù)蘇的迫切期待交織成復(fù)雜的治理難題。在此背景下,默茨政府推動對外政策的“歐洲化”,本質(zhì)上是德國在多重危機(jī)下尋求突圍的重要思路。
一是提振國內(nèi)經(jīng)濟(jì)競爭力。就職當(dāng)天,默茨表示歐盟才是德國的優(yōu)先發(fā)展方向。當(dāng)前德國工業(yè)面臨能源價格高企、供應(yīng)鏈脫鉤壓力以及數(shù)字化滯后的三重挑戰(zhàn),疊加美國關(guān)稅政策的擠壓,傳統(tǒng)出口導(dǎo)向模式已顯疲態(tài)。默茨在競選期間提到,應(yīng)借助歐盟集體談判力量制衡美國單邊主義,同時以共同政策推動歐盟內(nèi)部改革:一方面推動歐洲能源市場的整合以降低企業(yè)成本,借“歐洲芯片法案”加速產(chǎn)業(yè)升級;另一方面依托歐盟“全球門戶”計劃拓展海外基建投資,為德國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與設(shè)備出口開辟新空間。默茨的“歐洲化”思路既有助于規(guī)避單邊財政擴(kuò)張的債務(wù)風(fēng)險,又能通過深化歐洲內(nèi)部協(xié)作以賦能德國自身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如利用集體行動增強德國在綠色經(jīng)濟(jì)、數(shù)字主權(quán)等領(lǐng)域的話語權(quán),為維護(hù)德國工業(yè)競爭力創(chuàng)造空間。
二是彌合國內(nèi)政治分歧。從國內(nèi)政治層面看,“歐洲化”轉(zhuǎn)向也是平衡執(zhí)政聯(lián)盟分歧、抵御民粹浪潮的“減壓閥”。此前朔爾茨政府在財政緊縮、社會福利及移民政策議題上立場撕裂,極右翼選擇黨借反歐盟、反全球化持續(xù)擴(kuò)張,已威脅主流政黨基本盤。默茨政府試圖將政策重心轉(zhuǎn)向歐洲共同防務(wù)、移民配額機(jī)制等跨國議題,把國內(nèi)矛盾“轉(zhuǎn)化”為歐洲集體行動:例如在對非法移民出臺嚴(yán)格管控政策的同時,以歐盟邊境管理局改革替代單邊關(guān)閉邊境,以歐洲社會基金擴(kuò)容緩解國內(nèi)分配爭議等。這種策略既能維系執(zhí)政聯(lián)盟“斗而不破”的脆弱共識,又通過強化“歐洲公民身份”敘事回應(yīng)民粹主義的排外浪潮,為德國政治穩(wěn)定構(gòu)筑“歐洲安全網(wǎng)”。
三是重塑核心引領(lǐng)形象。相比朔爾茨政府的謹(jǐn)慎,默茨參與歐洲事務(wù)的態(tài)度顯得更為進(jìn)取,無論是在對美斡旋、強硬對俄、支持援烏等問題上都展現(xiàn)出積極的一面。這一政策轉(zhuǎn)向也折射出德國在全球變局中的角色再定位。面對中美博弈加劇與多極化沖擊,對外政策的“歐洲化”使德國能夠在外交上更加靈活地處理與各大國的關(guān)系,并以歐盟的名義開展外交行動,避免過度卷入大國競爭,增強自身的談判籌碼,更好地維護(hù)本國利益。同時在對外政策上主動向歐盟主流靠攏,爭取贏得更高話語權(quán)。這種“歐洲化”并非理想主義回歸,而是德國在實力相對衰微背景下,以多邊機(jī)制為支點延續(xù)影響力的選擇。

二、德國推動“歐洲戰(zhàn)略自主”:從理念到行動的突破?
近年來,德國與歐盟面臨跨大西洋關(guān)系松動、俄烏沖突持久化、歐盟安全與防務(wù)自主進(jìn)展緩慢等挑戰(zhàn)。內(nèi)部動蕩也削弱了德法等核心國家的領(lǐng)導(dǎo)作用。默茨能否帶領(lǐng)德國發(fā)揮引領(lǐng)作用,推動歐盟有效應(yīng)對危機(jī),成為外界普遍關(guān)注的焦點。
(一)強化歐洲防務(wù)自主化,推動構(gòu)建獨立安全架構(gòu)
俄烏沖突后,美國戰(zhàn)略重心加速向亞太轉(zhuǎn)移,特朗普政府的對歐安全承諾搖擺(如削減駐軍計劃)迫使歐洲重新評估單邊依賴風(fēng)險。默茨政府對此選擇突破“債務(wù)剎車”限制,豁免國防和安全支出限制,旨在實現(xiàn)北約軍費占GDP 2%的目標(biāo),并通過加大國防投入、加強軍事技術(shù)研發(fā)、參與歐洲防務(wù)合作項目等方式推動重構(gòu)歐洲獨立防務(wù)體系。德國新任外長約翰·瓦德普爾(Johann Wadephul)還主張整合法國核力量,推動建立歐盟快速反應(yīng)部隊。然而,歐盟成員國對于歐洲防務(wù)自主化的規(guī)劃與路徑難以達(dá)成完全一致。默茨政府仍需思考如何更好協(xié)調(diào)歐盟內(nèi)部立場,同時避免引發(fā)地區(qū)緊張局勢。
(二)推動歐盟經(jīng)濟(jì)政策協(xié)調(diào),應(yīng)對經(jīng)濟(jì)安全與去風(fēng)險
在地緣政治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一向重視出口和開放市場的德國與歐洲經(jīng)濟(jì)遭受極大沖擊。對此,默茨政府設(shè)立了5000億歐元的基建基金以及 1000 億歐元的氣候轉(zhuǎn)型基金等,以釋放德國在國防、綠色轉(zhuǎn)型以及經(jīng)濟(jì)復(fù)蘇等關(guān)鍵領(lǐng)域的投資空間,并主張推動歐盟各國就大規(guī)模財政刺激計劃達(dá)成共識,共同應(yīng)對經(jīng)濟(jì)下行壓力。同時,默茨呼吁加強歐盟貿(mào)易政策協(xié)調(diào),盡快啟動新一輪跨大西洋貿(mào)易談判,爭取在關(guān)稅協(xié)商談判過程中達(dá)成有利于歐洲利益的協(xié)議,并為歐洲企業(yè)開拓更廣闊的國際市場。此外,默茨政府延續(xù)對華“去風(fēng)險”思路,支持歐盟層面的貿(mào)易防御措施,重點推動供應(yīng)鏈多元化,審查5G、基礎(chǔ)設(shè)施等關(guān)鍵技術(shù)領(lǐng)域的對華投資,強化所謂“經(jīng)濟(jì)安全”。
(三)重啟法德軸心與魏瑪三角,鞏固歐洲核心領(lǐng)導(dǎo)力
經(jīng)歷了歐洲能源危機(jī)和俄烏沖突,德法之間分歧增加,德波關(guān)系遇冷,歐盟內(nèi)部大國之間的裂痕明顯。默茨上任后便首訪法國和波蘭,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和波蘭總理圖斯克(Donald Tusk)對德國在朔爾茨時代頻頻“隱身”之后再次走向前臺表露出強烈的期待。期間德法宣布成立“國防與安全委員會”,推動共同國防創(chuàng)新計劃,德波則是達(dá)成“支持烏克蘭軍事援助與東部邊境安全合作”聯(lián)合倡議。繼訪問法波兩國后,默茨還即刻轉(zhuǎn)場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與歐盟及北約官員會面。由此可見,默茨領(lǐng)導(dǎo)的德國新政府擁有重返歐洲的強烈意愿,并打算通過重啟法德軸心、激活魏瑪三角等歐洲外交機(jī)制,重塑歐洲核心領(lǐng)導(dǎo)力,在處理與中美俄等重要國家的關(guān)系時展現(xiàn)歐洲的團(tuán)結(jié)與自主,增強歐洲的話語權(quán)和影響力。
可以看出,默茨更強調(diào)“主動出擊”與務(wù)實合作。從經(jīng)濟(jì)復(fù)蘇到能源安全,從歐盟團(tuán)結(jié)到跨大西洋平衡,其“歐洲路線”正逐漸明晰。但德國目前的政治情況、經(jīng)濟(jì)困境以及歐盟內(nèi)部的各種矛盾分歧,都會制約德國提升影響力,對推進(jìn)歐盟多項競爭力政策的落實恐出現(xiàn)滯緩。接下來,德國是否能在復(fù)雜國際格局中平衡國家利益與歐洲責(zé)任,有效協(xié)調(diào)歐盟內(nèi)部立場,將成為觀察其外交成效的關(guān)鍵。

三、德國在歐盟對華政策中的角色:妥協(xié)者還是引領(lǐng)者?
作為一名大西洋主義者,默茨的對華態(tài)度較為復(fù)雜。一方面,他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及對華投資風(fēng)險,并在競選期間呼吁應(yīng)重新思考對華關(guān)系,在對華問題上應(yīng)形成統(tǒng)一的歐盟立場。另一方面,在勝選后則強調(diào)務(wù)實合作,承認(rèn)德中合作對提升德國經(jīng)濟(jì)和國際地位的價值。此次聯(lián)合執(zhí)政協(xié)議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默克爾時代對華“務(wù)實合作”的基調(diào),但在戰(zhàn)術(shù)層面延續(xù)了“去風(fēng)險”的特點。例如協(xié)議明確要求設(shè)立聯(lián)邦議院專家委員會,每年評估德中經(jīng)貿(mào)關(guān)系的“依賴性”并提出對策。可以看出,新政府試圖在維持經(jīng)貿(mào)基本盤的同時,也通過立法和審查機(jī)制構(gòu)建“防護(hù)網(wǎng)”,以回應(yīng)國內(nèi)對產(chǎn)業(yè)安全的擔(dān)憂。
與德國首部《中國戰(zhàn)略》描述的一致,此次聯(lián)合執(zhí)政協(xié)議也主張將對華戰(zhàn)略“牢牢植根于歐盟共同的對華政策中”,以歐洲為基礎(chǔ)制定對華政策,并與歐盟伙伴進(jìn)行更密切的協(xié)調(diào),積極推動歐盟內(nèi)部就處理對華關(guān)系達(dá)成一致,進(jìn)而實現(xiàn)德國從歐盟整體規(guī)模政治中獲得權(quán)力和影響力的戰(zhàn)略構(gòu)想。德國的選擇不僅關(guān)乎自身國際地位,更將關(guān)乎歐盟在與中國互動中的角色定位。結(jié)合默茨新政府的特點,未來德國將給歐盟對華政策帶來多方面的影響。
(一)經(jīng)濟(jì)利益驅(qū)動下推動歐盟對華合作與競爭的再平衡
在跨大西洋關(guān)系承壓與美國政策轉(zhuǎn)向的背景下,由具有成熟對華交往經(jīng)驗的聯(lián)盟黨和社民黨組成的新政府仍將以經(jīng)濟(jì)理性驅(qū)動對華戰(zhàn)略,把強化對華經(jīng)濟(jì)合作視為提振國內(nèi)經(jīng)濟(jì)的關(guān)鍵舉措,并在重構(gòu)中歐關(guān)系過程中將穩(wěn)定雙方經(jīng)貿(mào)合作作為戰(zhàn)略優(yōu)先項。一方面,德國將繼續(xù)尋求擴(kuò)大與中國在技術(shù)創(chuàng)新、市場準(zhǔn)入及產(chǎn)業(yè)投資等領(lǐng)域的合作空間,通過中歐務(wù)實合作提升歐洲整體的產(chǎn)業(yè)競爭力。另一方面,德國將延續(xù)對華“去風(fēng)險”思路,推動構(gòu)建歐盟對華“有限合作+制度性競爭”框架,鞏固歐洲企業(yè)在傳統(tǒng)優(yōu)勢產(chǎn)業(yè)的領(lǐng)先地位,并通過投資篩查機(jī)制、關(guān)鍵技術(shù)出口管制及供應(yīng)鏈韌性等計劃,逐步降低在關(guān)鍵領(lǐng)域?qū)χ袊囊蕾嚒?/p>
(二)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差異下推動歐盟保持對華施壓
中歐在政治制度與治理模式的結(jié)構(gòu)性差異,促使德國及其他歐盟成員國持續(xù)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盡管美歐關(guān)系面臨挑戰(zhàn),但雙方在價值觀同盟與科技管制領(lǐng)域利益趨同,使德國對華政策既受北約框架下的對美安全依賴束縛,又需調(diào)和歐盟內(nèi)部立場分歧。短期內(nèi)德國仍將在涉疆、涉港及人權(quán)議題上保持對華施壓。然而,德國可憑借"戰(zhàn)略斡旋者"身份推動歐盟形成對華有限共識,建立緩沖機(jī)制弱化美國遏制政策對中歐經(jīng)貿(mào)的沖擊,最終形成"價值觀外交"與"戰(zhàn)略自主"并行的政策架構(gòu)。這種在跨大西洋依存與歐洲自主之間尋求動態(tài)平衡的做法,本質(zhì)上也是歐盟多重地緣訴求的現(xiàn)實投射。

(三)全球治理合作下強化歐盟對華的規(guī)則與標(biāo)準(zhǔn)競爭
默茨政府預(yù)計在延續(xù)多邊主義傳統(tǒng)的同時,將繼續(xù)把歐盟作為其參與全球治理的核心載體,并支持倡導(dǎo)歐盟在綠色轉(zhuǎn)型、人工智能、公共衛(wèi)生、國際減貧等全球議題與中國展開務(wù)實合作。但與此同時,德國也致力于強化歐盟的議程設(shè)置能力和標(biāo)準(zhǔn)輸出策略。例如在之前的中歐數(shù)字伙伴關(guān)系談判中,德方堅持要求中國企業(yè)在數(shù)據(jù)跨境流動中遵守歐盟《通用數(shù)據(jù)保護(hù)條例》(GDPR),以此作為技術(shù)合作的前提。這種“規(guī)則綁定合作”的模式,實質(zhì)是希望通過多邊平臺將歐盟標(biāo)準(zhǔn)嵌入國際技術(shù)治理體系。此舉既有助于重塑歐洲的全球競爭規(guī)則,也是鞏固德國在歐盟內(nèi)部領(lǐng)導(dǎo)力的現(xiàn)實需要。因此,未來中德及中歐不可避免將繼續(xù)面臨全球治理規(guī)則和標(biāo)準(zhǔn)的話語權(quán)競爭。
默茨領(lǐng)導(dǎo)下的德國正試圖在“歐洲化”框架下平衡國家利益與歐洲責(zé)任。其政策能否成功,既取決于國內(nèi)共識的凝聚,也考驗其在歐盟內(nèi)部的協(xié)調(diào)能力。對華政策上,德國或?qū)缪荨皠?wù)實引領(lǐng)者”,推動歐盟在對華合作與競爭間尋找動態(tài)平衡,而這一過程無疑將深刻影響中歐關(guān)系的未來。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