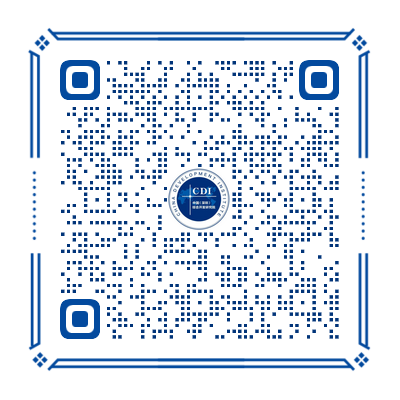唐杰:中國經濟轉型與動態競爭創新發展
時間:2016-05-27 09:31
【綜研微語】從長期觀察的視角來看中國經濟,持續35年的中國經濟奇跡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奇跡的基本經驗是什么?奇跡還可以持續嗎?奇跡結束之后會是什么?近日,藉唐杰教授新著《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出版之機,我院舉辦中國經濟轉型座談會,邀請到唐杰教授分享他的思考,座談會還邀請郭萬達、劉憲法、趙登峰、趙成、孫浩、龍隆、楊柏、王瑞平、金心異、謝亞軒、鄒藍、鐘若愚、李帆、曾廣勝等研究同仁參加,我們整理了部分會議發言,以飧讀者。

感謝大家從各個角度所做的精彩評論。我簡單回應一下。2014年南開研究生微信群就中國經濟未來走向討論了大約七八個月時間,核心問題是對過去35年怎么看?對未來35年怎么看?共同看法是,過去35年的成就會是未來35年發展的基礎,當然也有可能成為包袱。
只要我們從長期觀察的視角來看中國經濟,一定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持續35年的中國經濟奇跡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奇跡的基本經驗是什么?奇跡結束之后會是什么?會不會出現一地雞毛的結果?當然,提出和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有一個合適的時空架構。

唐杰:博士生導師、哈工大(深圳)籌建辦臨時黨委書記、深圳市原副市長
一、從時間軸上觀察中國經濟長期發展過程與性質變化
我們嘗試以康雍乾盛世作為起始的觀測點,以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作為中間觀測點,以深圳作為走向未來的觀測點,簡單說是希望在過去300年、30年和未來30年的連續時間范圍內,進行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動態分析。
一是回望300年的康雍乾盛世,我們看到是一個真正的盛世,是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階段,農耕文明創造的最后一個奇跡。大清朝實施了歷史上最徹底的鼓勵農業、輕徭薄賦的供給側政策,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和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全球化紅利。一百年的時間里經濟總量上升了三倍,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國家與社會的財富空前增加,但令人驚訝的是經濟總量增長的倍數差不多就是人口增長的倍數,人口從一億達到三億,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生產率沒有什么提高,除了數量擴張沒有生產方式的質的變化,盛世過后留下了一地雞毛,留下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
二是回顧30多年的改革開放, 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不再是簡單人口增加的數量增長,龐大的經濟總量背后是人均收入及社會生產率的大幅提高,教育科學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加入WTO后的十年里,中國大陸新增加的經濟總量相當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總計的80%,超過了中華文明歷史的總和。相對于300年前由廣州十三行壟斷國際貿易,現代中國的對外開放從經濟特區,沿海沿邊開放演變為全面開放,以史無前例的開放心態與全球化對接,最大限度地獲取了經濟全球化的利益,推動了持續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不過認真觀察,不能不承認,過去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與康雍乾盛世時代還是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混雜了太多的簡單的數量型擴張的因素。
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回落,人們先是猜測是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外部因素引起了中國經濟增長短周期下落。現在新的共識在慢慢形成,中國經濟增長回落主要不是外部因素,主要不是冠名“四萬億”的反危機措施短期因素,而是內生的長期動態下降。過去三十余年我國經濟在獲得人口紅利,投資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同時,極大地放大了數量型增長領域范圍和能量。康雍乾盛世終結于有限土地開發殆盡,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將終結于三個紅利的終結。過去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百米沖刺,中國經濟需要調整姿態,轉向跑得穩、跑得遠、持續時間更長馬拉松。中國奇跡要從實現從數量型擴張全面轉向創新型增長。
三是展望未來30年,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是中國經濟繞不過到的坎,短期穩定經濟宏觀政策非常重要,但離開了發展方式轉變又是沒有意義的。深圳是我國經濟從數量型高速增長轉向創新發展突出案例。作為一個由無限傳奇故事編織起來的年輕城市,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的經濟總量僅為香港的千分之二,目前已經是香港的90%。在深圳之前,全球似乎還沒有哪一個城市能夠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實現由農業經濟向知識信息經濟的連續跳躍。本世紀初,深圳人均GDP只是臺灣1/3,2013年已經超越臺灣。深圳已經成長為全球最重要移動通訊裝備生產和技術創新城市,正在成長為生物、新能源與材料科學的引領中心。深圳是中國人均專利擁有量最高的城市,是擁有PCT國際專利最多的城市,是全球重要的科技創新成果、創新人才和創新性企業的聚集地,是產業結構持續升級的城市,更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是一個經濟增長率持續降速的城市,三十五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約為30%,目前已經穩定地下降至8-9%。百米沖刺不容易,從百米沖刺轉向馬拉松更難,總結研究深圳轉型成功的經驗應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空間軸上的橫向比較有助于發現普遍性趨勢
時間軸是簡單地自己與自己比,加入空間軸后,我們可以觀察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同一時期發生的相似現象,從中觀察經濟發展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找到我們與共同特征的異同,看到我們優勢與差距。
一是康雍乾盛世最終煙消云散的根本原因?在歷史中穿行讓我們最感震驚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沿著既有的軌道前行取得了輝煌成就,卻在前進的路上迷路了,走丟了,走進一個難以掉頭的死胡同。而與康雍乾盛世同時的歐洲是,確是伽利略、牛頓等大科學家輩出的時代,歐洲點燃了世界科技革命火炬,經歷了科技革命,產業革命,政治革命的歐洲,跨越亙古引入了全新的文明,進入了馬克思所贊譽過的,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的新時代。沒有科學發現支持的、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不能有效復制的傳統農耕文明的創新活動,歷經成百上千年積累起來的成果,在幾十年,幾年,甚至是幾天、幾個小時內就被以科學發現為基礎的工業文明所超越,被遠遠地甩在后面。吃苦耐勞的能工巧匠,辛勤勞作的農民,面對科學技術的大規模突破迅速地喪失了競爭力。古老的中華文明,而不僅是康雍乾盛世,轉眼之間就被超越,被拋離,在競爭中走向了衰敗。
二是在第二個時間節點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奇跡是改變了當代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中國奇跡是發生在中國,離開了中國談不上中國奇跡。勞倫斯.薩默斯等指出,在現代歷史上,只有極少國家和經濟體能夠實現連續十年6%以上的超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打破了一般趨勢,締造了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長的高速增長期。過去三十五年中國經濟增長每年為9%;生活水平每8年翻一番,三十五年增長了16倍,由此帶來了更多的經濟變化、更多的繁榮、更多的創造、更多的生產、更多的生活方式的轉變。發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廣,與世界經濟互動如此之強,在工業化史,在世界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是定將載入史冊的經濟奇跡。
上個世紀開始的時候,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10%,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下降為5%,改革開放的開始的時候仍然是5%,三十五年后上升為四分之一。沒有解放思想,沒有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沒有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不可能在總體穩定下,快速平滑地實現市場經濟體制對傳統計劃體制的替換。這是一個極富中國特色的制度轉軌模式,是三十年持續高增長的中國奇跡的基礎。
當然,離開了世界也無法解釋中國奇跡。盡管各國的稱呼不同,但實施改革開放是過去三十年的世界性現象,是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全球經濟增長因此而加快,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是新興市場經濟體進入了追趕行列。中國奇跡并不在于高速增長,只是高速增長的時間更長,涉及的人口更多,取得的成就更大。
而今三十年的高速追趕過程正在消退,新興經濟體不約而同地進入了經濟減速期。當我們說,外部因素或更直接地說,美歐日經濟衰退引發減速時;反面的看法也是成立的,新興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已經歷史性回歸到占世界總量50%以上,因此新興經濟體的減速是構成世界經濟減速的直接原因。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集體減速的現象直接誘發了關于中等收入陷井的關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民族獨立與民族自主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個甲子過去了,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卻鮮有從落后國家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案例。從1950年到2008年間,只有13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了高收入行列;有28個經濟體與美國的人均收入縮小了10個百分點或更多,其中只有12個不是石油、鉆石生產國或歐洲國家;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從高收入滑落為中等收入國家,此外的絕大多數仍然處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盡管相當多的國家經歷過快速甚至是高速增長。這就是中等收入陷井。中等收入陷井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表現形式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都有過度依賴低要素價格,模仿期有較高的投資回報和突然擴張的全球市場,主要以做加法方式進行數量擴張的追趕。顯然,這與康雍乾盛世展現的傳統經濟增長并沒有本質區別,或早或晚一定會因邊際收益快速遞減,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下降,而歸于停滯。
三是自工業化以來,發達經濟體的平均長期增長率不過是略高于2%,不斷遇到危機但卻沒有掉入陷井呢?這是在討論中經常引起我們困惑的問題。我們嘗試將之比喻為龜兔賽跑,為何高速奔跑的兔子總也追不上爬行的烏龜?一般人講故事會說,這是因為兔子跑的時間少,休息的時間多。我們嘗試這樣看問題,烏龜為何能夠緩慢地但不停地前進?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們集中觀察了一個現象,歐洲、北美與日本崛起于工業化,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但同時是全球最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中心,或者說是因為成長為科技創新中心才成長為制造中心。當發達經濟體不再是以制造業的規模和數量衡量的制造業中心時,仍然是世界上科學技術創新的中心,把控著以質量衡量的高端制造。發達國家不斷遇到衰退、滯脹和危機,就是不會掉進陷井。這如同于龜兔賽跑中,烏龜跑得慢卻可以不斷地從創新中獲得持續的動力,兔子跑得快但不斷撿拾烏龜扔下的包袱,因此休息的時間會更長。從故事走到現實不難發現,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發展中國家,不是資源供給者,就是低端制造者或者干脆就是裝配中心。沒有創新能力的兔子跑得快卻不可以持續,封閉在一個環形跑道上跑跑停停。
在時空框架里回顧與穿梭,我們看到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工業文明興起于科學技術創新,在持續增長過程中,空間上出現的國別之間,經濟體之間的顯著差距可以歸因于是否具有可持續的鼓勵創新制度,以及是否具有激勵創新的國際競爭力。依靠模仿的追趕過程,可以實現短期高增長,但一定會因為模仿而不是創新而從減速歸于停滯。處于現代經濟增長邊緣的新興經濟體要走向舞臺的中央,沒有捷徑,只有學習借鑒先行者建立起具有世界競爭力的激勵創新的制度。
在時空框架中回顧與穿梭,我們發現深圳堪稱從模仿型追趕走向創新追趕的范例。深圳經濟特區起于工業化為空白的農耕文明,在發展的初期以三個為主實現了高速起飛,“以外商投資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不到十年成為全球重要的OEM生產基地。第二階段OEM型產業大規模外遷,推動深圳走向模仿性創新的生產制造,出現了廣泛的山寨現象,有了Made in SZ(Shenzhen)的戲稱。當然,模仿是人類的天性,沒有對生物界的模仿,大量科技創新都不會產生。這也是德美日韓都曾經歷過的憑借模仿形成大規模生產的階段。但關鍵是如何從簡單模仿走向創新。深圳和經濟發展從本世紀初開始,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以華為、BYD、華星光電等為代表,深圳進入了以自有核心技術支撐的大規模制造的時代,招商銀行和平安集團為代表的創新性金融業開始崛起。“十二五期間”是深圳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有了鮮明的創新發展的特征。深圳已經在新一代無線通信技術領域擁有了占全球1/5的專利,基因測序分析與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顯示與虛擬現實技術等領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自主創新能力,擁有核心技術并在全球產業鏈關節點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創新型企業有如潮水一樣奔流而來,創新創業和企業家群體的崛起成為深圳象征。
三、我們發現了什么?
一是短期經濟衰退與長期增長潛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比如說,硅谷歷經衰退仍然是全球創新高地。深圳歷經發展的瓶頸,卻總是令人驚訝地煥發生機。關鍵在于,短期的危機與衰退并不否定硅谷和深圳是新模式的代表。當我們研究比較優勢的時候,可以看到300年前中國的比較優勢是人少地多的優勢,人口不斷膨脹,土地變得稀缺,過度開墾變成土地急劇邊際收益遞減,優勢就沒了。但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里,康雍乾盛世并沒遇到嚴重的短期衰退,除了幾次重大的自然災害之外。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成了新的比較優勢,但若有一天人口紅利沒有了,投資紅利沒有了,全球化紅利也沒有了,也會出現邊際收益大幅遞減,平穩的短期經濟運行會與長期增長潛力大幅度下降相碰撞,此時短期總需求政策幾乎是無能為力的。
二是短周期危機或衰退是防止結構扭曲和產能過剩長期化的重要機制,具有修復長期增長潛力變化的效果。不同時期的產能過剩和結構扭曲形式各異,又具有高度的內生一致性,經濟繁榮期產生的投資沖動和跟風式的蜂擁而上。問題是,產能過剩是一個泥沙俱下的狀態,優質企業和劣質企業魚龍混雜。繁榮期,優質企業收益高,劣質企業收益低,但活得也不錯。危機和衰退期,優勢企業收益降低,劣質企業就不能生存,過剩產能便歸于消失。危機或衰退就是短期的,同時修復可能出現的長期增長潛力因邊際收益下降而下降的趨勢。
三是結構扭曲和產能過剩源自于企業對利潤的追逐,消除結構扭曲和產能過剩源自優質企業擊敗跟風的劣質企業,使其面對無法承受的虧損而退出。優質企業能夠成為優質,源自于占領市場競爭的制高點,要做到這一點只能一個可能,持續不斷地創新。在空間上,優秀企業數量規模和成長性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比較競爭優勢的核心,而優秀企業的產生一定源自于存在著一個優秀企業家群體。從此意義上說,300年前的科技革命能夠演化為產業革命,并且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持續不斷的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是因為偉大企業不斷的涌現。附加在生產裝備上的新科學技術先是使現代經濟增長具有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特征,而后又推動了新科學技術不斷產生,企業競爭力從機器裝備水平不斷提升,逐步發展為綜合了高素質人才與高水平的專利標準的創新競爭,現代經濟增長不斷拋棄數量加法,創新在增長中的主體地位不斷提升,創新前沿不斷地向前推進。
四是創新來自于競爭,競爭依賴于高效規范有序的市場機制,這是一個保證優勢企業可以獲得創新收益的法治化市場。從此意義上說,政府存在的最大理由是保障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創造出不斷升高的市場競爭力度,這是最重要的公共產品。馬克思最早觀察到工業革命將進入大企業時代,熊彼特最早提出了大企業是創新主體的假設。隨著科學與技術發現演進,中小企業正在成為創新中堅力量,創新型中小企業依賴科技突破擊敗大企業,成長為新的偉大企業正在成為一個普遍的經濟現象。面對新的企業成長生態,政府應該做的是不分親疏、不拉偏架,不袒護落后,放手讓企業競爭,放手讓優勢企業擊敗劣勢企業。
最后,在時空框架中大跨度的觀察使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每個國家和地區在同樣的時間軸上都有著各異的發展狀態,向前走,當然要從自己的條件出發;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條件差異再大,但從數量型增長轉向創新增長的方向又是一致的,轉型所依賴制度條件是一致的。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演進的過程,演進的全部含義是走入動態競爭創新的路徑,而無論是沿著泥濘的小路,還是在荊棘叢生中開辟出一條通道。如此,動態比較優勢與初始狀態結構差異就是無關的。

“持續的高投資率要能帶來高資本邊際資本產出增長率,中長期的資本邊際產出率要大于實際利率,這是保持我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核心條件。如果不能實現這一基礎條件,無論短期總需求管理政策有多成功,也不可能保證我國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
本書由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資助出版,
現已發售
京東 http://item.jd.com/11909105.html
當當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950477.html
(0)